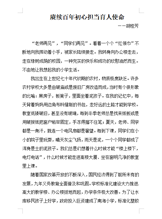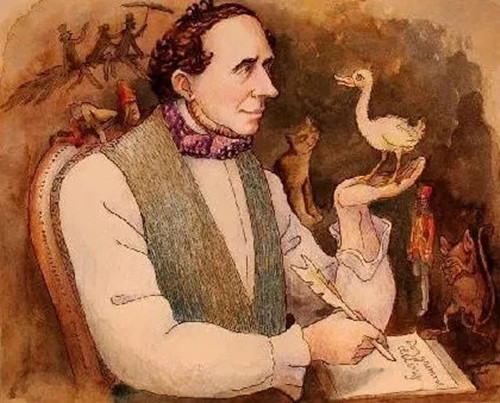永远的老师 永远的先生
分享
133203
今年2月1日,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主要创办人宿白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日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举行宿白先生追思会,来自各相关单位和先生不同年代的学生代表及家属代表,齐聚一堂,回顾先生的崇高精神和学术风范,感念先生对后辈的关爱和提点,追忆先生在教书育人、治学求真中的点点滴滴,重温先生的音容笑貌,共同缅怀大家永远的老师永远的先生。
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缅怀宿白先生。回顾先生为中国文物考古界做出的贡献,追忆先生的点点滴滴。
北京大学教员是先生唯一认可的身份。宿白先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集大成者,他强调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历史时期考古的诸多领域。先生广泛吸收海外资料,搭建了石窟寺研究的时空框架。先生关注文物保护事业,呼吁加强新疆石窟寺保护工作,并努力解决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先生一生著作等身,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学界奉为圭臬,《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先生的高洁品质,照耀和温暖着周围的人。
作为从北京大学考古系走出的学生,我有幸曾受教于先生,这里回忆几点与先生交往的感受。首先,先生教学认真。他关心学生的毕业去向,希望学生回到地方考古所,推动地方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生关注石窟寺保护研究工作,几次询问敦煌、龙门、阿斯塔纳考古报告的出版工作。先生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工作也十分重视,几次就相关情况询问文物部门的同志。先生对文献和图纸十分敏感,他强调要将城市考古的成果落实到地图上,这也对后来城市考古工作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先生十分谦虚,面对学生的提问,熟悉的领域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太熟悉的领域则会大方承认,建议同学去找相关领域的其他老师。
我们今天追忆先生的风范、感怀先生对后辈的提点,就是要继承先生的精神,主动承担起保护、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责任,向世人展现真实的古代中国,唯如此才不辜负先生的嘱托和期望。
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宿白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翠花胡同和东厂胡同留下了太多先生的身影。先生和考古所第一代考古学者们一起,为创建中国的考古专业呕心沥血。正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我们的学科体系才得以日臻完善。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设立之时,考古教研室主任一职由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担任,宿先生任副主任,但具体的工作大都是由宿先生领导实施。宿先生是整个考古学界的老师,他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八宝山送别宿先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在先生身旁长跪不起,当时我意识到,先生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们。
宿先生还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考古组和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先生都付出了很多心思。起初,宿先生带着徐苹芳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起草规划学科建设,重视学工建设,历史时期考古学科体系可谓由先生一手创办。在这一过程中,先生也与中国社科院交集颇多。先生桃李满天下,中国社科院是一个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地方,但是先生培养出的北大学子占了很大比重。到今日,我认为,先生培养出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说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奠基人、中国考古学科体系的规划者、北大考古的引领者,恰如其分。
作为81级北大考古学生,当时有同学去侯马实习,宿先生专程前来探望,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山西考古学的课,让我深深感到先生学问之博大精深。先生虽主攻历史时期考古,但从新石器时代讲起,体系逻辑清晰,让我真正认识到先生思考的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建设。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仅在做学问,更在做人。他曾给同学写长信,具体到如何与地方工作者打交道。先生的风范不仅体现在扎实严谨的学风,更体现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教我们如何从一点一滴做起的精神。我们今天在这里缅怀和纪念先生,继承先生遗志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我们本分的事情,把考古事业推向前进。
张广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
众所周知,宿白先生的一系列著作都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他对文物出版社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先生很早就与文物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61年前,即文物出版社成立的1957年,先生编写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到1999年间,相继出版了《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等经典之作。2009到2012年,先生年届90高龄之际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其中《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辑录了先生在《文物》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篇目全部是先生亲自拟定的,书的开本和篇幅也不大,但内容丰富扎实。《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其中有4种收录了先生手绘的线图,实为难能可贵。上述这些著作同样值得我们后学认真研读、学习。当我们看到先生著作中的手绘线图时,倍感亲切,也从中体会到先生的认真、细致、严谨、一丝不苟。据一些编辑回忆,先生即使到了晚年,在出版著作的过程中,仍坚持亲自批改书稿校样,从不让人代劳。年届九旬的老人对待书稿严谨求实、毫无虚浮的认真态度,为我们做好编辑工作树立了榜样。而且,对于校样的修改,先生还要给编辑讲解修改的原因。这些讲解,使编辑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文字上都受益匪浅。
宿先生除了署名的著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对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图书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至第五批》《中国文物精华》等书稿的体例、内容予以审定,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撰写图版说明。做这些图书出版工作中的基础工作,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先生为文物考古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宿先生曾经对我们的一位编辑说过:“不要求每个人成为学术大家,但是,在本职岗位上做好考古学的基础工作,就是为考古学做贡献。”我们作为文物考古图书出版人,编辑出版考古报告等文物考古类图书,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先生所说的基础性工作,是服务于文物考古事业、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先生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是亲切的鼓励。做好文物考古图书的编辑出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宿先生虽然已经告别了我们,但是,他还留下了未了之愿。其中编辑出版《中国陶瓷史》就是其中之一。组织编撰工作的徐苹芳先生、张忠培先生也已相继离世,编撰工作遇到了巨大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强力支撑,有文物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中国陶瓷史》的出版将是对宿先生的最好纪念。
为了表达对宿先生的深切缅怀,在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之际,文物出版社在第一时间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提出了编撰出版《宿白先生纪念文集》的愿望。今天纪念文集编撰工作正式启动,文物出版社将全力配合,做好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对宿白先生给予文物出版社的关心、支持、帮助,给予出版社的恩惠,文物出版社全体同仁将永远铭刻于心!
张连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宿白先生出生在沈阳,在离开沈阳求学后,一直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多次向先生汇报沈阳考古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果,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起讨论,说起家乡的一些历史建筑、民俗趣事,更是如数家珍。先生多次流露出想回家乡沈阳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但终未能成行,成为一件憾事。
宿白先生心系家乡的考古事业。2007年,《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和出土文物卷、《沈阳考古文集》结集准备出版,我们恳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慨然允诺,并指导我们:要写好发掘简报、发掘报告,你们所做的报告,可以表达初步观点,更要紧的是如实反映古代遗存情况。
2010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筹备文物整理基地时,恳请先生为基地题词并为全所题写所训。先生欣然题写所训:“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先生多次向我们强调:在城市考古中,可以对有代表性的发现做适当的保护性展示,给人们提供有意味的历史信息,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底蕴。而今,“清盛京城德盛门瓮城遗址”“汗王宫遗址”和“豫亲王府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已成为沈阳的城市新名片。
宿白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后辈学习的楷模。他的开拓创新精神、杰出成就和高尚品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青山巍巍,绿水滔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我国考古界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尊师重教。前不久,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一百二十周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展览中有一件特别的展品,是一个放有白沙宋墓墓砖的木箱。这是一件看似普通但饱含很多内容的展品。展览开幕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用这件展品,向宿白先生致敬;用整个展览,向中国考古致敬。北大考古一路走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创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还有先生未竟的事业,都是我们未来努力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先生。
吴荣曾:我1953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宿白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中间考古专业的领导换过几波,但实际负责管理考古专业的还是宿先生。先生工作能力很强,行政工作也做得很好,从那时起,就成为考古专业的实际负责人。当时同学接触最多的也是宿先生,所以对宿先生也比较了解。课程安排、人员调配等大小事务都由先生操办。当时考古专业正值草创之时,教师紧缺,正式教师就是宿先生和阎文儒先生,其他教师都是外聘过来的,宿先生外请来的老先生很多。宿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开设了美术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门课。当时人手少,宿先生主攻唐宋考古,秦汉考古请过王仲殊先生,宿先生也曾亲自上阵,并且表现出了很深的造诣。
宿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还多才多艺。先生有刻章的喜好,但不张扬,可能外面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先生还有一项技能,就是素描能力很高。他曾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跟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水平不输专业人员。总体来说,在我和宿先生这么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先生的品质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知识渊博、二是治学谨严。
严文明:我高中时期喜欢数理化,进校本来报考的是物理系,是苏秉琦先生找我谈话我才选择了考古专业,但后来引我走上考古道路的是宿先生。苏秉琦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在北大是兼职,不负责具体事务,印象中苏先生主要提供选择实习地点的方案,因为当时北大实习是和考古所挂钩的;而具体的教学工作,包括实习的组织,是宿先生在操办。第一次北大自己组织实习是1957年的邯郸实习,就是宿先生带队。
宿先生对于教师和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北京大学的考古教学能够走上正道,能够比较快速的发展,第一功劳当归宿先生。我做讲师的时候,讲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宿先生来进行教学检查,提出了好多意见,有根有据,让我汗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年轻教师的成长很有帮助。宿先生不是只对别人要求高,他首先是严于律己。
先生治学成功,有关键一条就是“勤”。先生认为早上安静、效率高,因此每天四点起床,就开始看书。这里举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宿先生第一次去美国,就一头扎进国会图书馆,因为那里有三本国内没有的书,他就手抄回来。后来一起去台湾开会,会议结束后台湾学者邀请我们游玩,宿先生却说这边有几本大陆没有的书,他也要手抄回来。于是我们在台湾玩了十多天,宿先生就在图书馆泡了十多天。因此宿先生的成就,跟他的勤奋有很大关系。我想起高尔基说过,天才就是聪明加勤奋,这用在宿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况且他还是比一般人更聪明,也更勤奋。正是聪明和勤奋的结合,造就出了这样一位巨匠。
宿先生对待工作同样认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主持下成长起来的。当初筹备成立考古系的时候,校方对于系主任的人选倾向于宿先生。一般这种有头衔的事情,先生往往拒绝,但那次却很爽快地接受了,并让我来做副系主任。宿先生一直对考古专业和考古系的建设等教育工作十分上心,说他是中国考古教育的奠基人,毫不为过。先生是一棵参天大树,先生的业务水平我无资格评论。我们纪念、追思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的精神,不然也不配做先生的学生。
杨泓:我是在六十五年前入学的。我入学去看望阎文儒先生,阎先生就带我去见了宿先生,我应该是班里第一个到校第二天就见到宿先生的。大二的时候跟着邓先生写论文,也是先去请教宿先生,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到大三写学年论文,就是后来的高句丽壁画石墓的文章,也是蒙宿先生的指导。可以说我学会写论文,就是宿先生带出来的,我一辈子也是沿着先生教出的道路上走。之后在中科院考古所里,就有机会和先生共事研究了,主要有两项:一是当时尹达组织编写“十年考古”,成立了编写组,宿先生是考古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组的组长就是宿先生,成员是我和徐苹芳,于是就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二是后来编写《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清考古的学术分支,宿先生是主编,徐苹芳是副主编,我是成员,由此也就认真地跟先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和先生六十五年的师生关系,想说、可说、能说的太多。先生的学问、人品,我是完全无法望其项背的。先生虽然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严肃的,但私下里其实也是个很风趣的人,之所以多数时间看起来严肃,主要是先生要求严格、做事认真。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表现得比很多党员都够中国共产党要求的高标准。宿先生教我的东西我受用了六十五年。先生走了,我也没有老师了,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也是我的遗憾。
徐光冀:宿先生确实是文物考古界的巨人、参天大树,是我们在座各位、更是考古界永远的老师。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合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我是1954年入学,当时大部分教师还是外部人员,来自中科院考古所、古脊椎所(当时叫新生代研究室)、故宫等单位。北大自己的老师就是宿白先生和阎文儒先生。专业创办之时,苏秉琦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是副主任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很多中间的联络性工作都是宿先生在做。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不能体会其中的艰辛;工作之后,才体会到先生当时的呕心沥血。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发展实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由于先生的付出,不到十年,也就是1960年前后,考古系的主要课程都是由本校教师承担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宿先生当时主要承担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体系都是先生自己谋划和组织的,现在这个体系已经推广到了全国。把考古资料和文献结合,是先生创设的历史时期考古教学样板。对于历史时期城址、墓葬的研究方法,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初,国家文物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文物保护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委员会停止活动后,宿先生仍在为文物保护工作积极奔走,例如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规划。在此期间,先生也确实检查了很多考古工地,直到80岁还在全国跑点。
中国考古学会是个很好的学会,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宿先生从一开始就是理事,而且是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到第三次大会就担任了副理事长。1995年正处在筹备来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过程中,当时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住院,他给常务理事会写了亲笔信,委托宿先生主持常务理事会工作。宿先生顶着压力接下了任务,仍坚持按照会章由常务理事会组织筹备。学会作为民办组织,一直都是组织纯学术活动,受到了民政部的表扬。先生为考古界的团结作出了榜样。
樊锦诗:我们都知道,石窟寺考古的体系是宿白先生创立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是先生最关心的两个地方。先生和敦煌结缘的时间很早。解放后,文化部接管当时的敦煌研究所,就派先生来勘查,这是先生和敦煌的交集之始。1955年,正式的考古调查开始。现在人们提到很多保护方面的问题,先生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看出来了,只是那时候没有太多可以相配合的保护手段。举一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敦煌窟檐破败甚重,是先生按照《营造法式》的记载进行了保护修复。现在说敦煌保存下来了5座唐宋窟檐,这都是宿先生等老一辈考古人的功劳。后来也是宿先生向文化部建议,认为风沙导致石窟的断裂是敦煌面临的最大问题,才有文化部下达批示予以保护。北大的独立考古实习,第一次是去邯郸的石窟,第二次就是在敦煌。可以说,中国石窟寺考古体系真正拿出来,也是在敦煌。后来先生系统讲授了敦煌七讲,成为了敦煌研究院发展的转折点,大家才开始明白怎么搞石窟寺研究,我自己也是一生受益。我在敦煌做的一点工作,都是先生教出来的,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先生的教诲我们终生难忘。
李仰松:宿白先生培养的学生很多。我1950年就来北大了,是文学院博物馆专业第二届学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到处搞建设,经常发现文物,地方上的考古发掘水平跟不上文物出土的速度,于是北大就开办了考古训练班。训练班一共四届,培养了360多人,其中很多回到地方上都成了专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办文物考古训练班是十分必需的,宿先生负责训练班的教务工作,很忙、很辛苦,这都是宿先生的贡献。先生去世让我很伤心,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考古后辈的楷模。
雷从云:先生是一棵大树,一直心系着他的学生。先生非常关注我国文物对外交流,关心文物对外展览。1971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成立,那时候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宿先生任陈列组组长。1980年我进入交流中心,到2011年退休,在这21年间,我应该算是和宿先生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我主办的69项展览,有一半以上都请教过先生。
宿志一:说实话,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很了解。我走的是理工路线,对于父亲的学术路线、学术水平并没有很多概念,直到最近看很多老师对父亲的追思,才填补了我对父亲认知上的一些空白。关于父亲的为人,我就说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现在不少人的名片上都会印上很多头衔,但在父亲的名片上,只有“北京大学教授”一项。我曾就此问过他,他说我没有多少成绩,就是当老师而已。父亲是一位踏实、简单的人。(以上内容根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关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
今天我们在这里,深切缅怀宿白先生。回顾先生为中国文物考古界做出的贡献,追忆先生的点点滴滴。
北京大学教员是先生唯一认可的身份。宿白先生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创建者和集大成者,他强调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以一己之力,开创了历史时期考古的诸多领域。先生广泛吸收海外资料,搭建了石窟寺研究的时空框架。先生关注文物保护事业,呼吁加强新疆石窟寺保护工作,并努力解决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先生一生著作等身,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学界奉为圭臬,《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先生的高洁品质,照耀和温暖着周围的人。
作为从北京大学考古系走出的学生,我有幸曾受教于先生,这里回忆几点与先生交往的感受。首先,先生教学认真。他关心学生的毕业去向,希望学生回到地方考古所,推动地方考古事业的发展。先生关注石窟寺保护研究工作,几次询问敦煌、龙门、阿斯塔纳考古报告的出版工作。先生对云居寺石经的保护工作也十分重视,几次就相关情况询问文物部门的同志。先生对文献和图纸十分敏感,他强调要将城市考古的成果落实到地图上,这也对后来城市考古工作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先生十分谦虚,面对学生的提问,熟悉的领域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太熟悉的领域则会大方承认,建议同学去找相关领域的其他老师。
我们今天追忆先生的风范、感怀先生对后辈的提点,就是要继承先生的精神,主动承担起保护、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责任,向世人展现真实的古代中国,唯如此才不辜负先生的嘱托和期望。
朱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宿白先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翠花胡同和东厂胡同留下了太多先生的身影。先生和考古所第一代考古学者们一起,为创建中国的考古专业呕心沥血。正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努力下,我们的学科体系才得以日臻完善。1952年北大考古专业设立之时,考古教研室主任一职由考古所的苏秉琦先生担任,宿先生任副主任,但具体的工作大都是由宿先生领导实施。宿先生是整个考古学界的老师,他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八宝山送别宿先生的时候,我的老师在先生身旁长跪不起,当时我意识到,先生的影响一直伴随着我们。
宿先生还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考古组和中国考古学会的工作。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组织层面,先生都付出了很多心思。起初,宿先生带着徐苹芳先生和其他老师一起起草规划学科建设,重视学工建设,历史时期考古学科体系可谓由先生一手创办。在这一过程中,先生也与中国社科院交集颇多。先生桃李满天下,中国社科院是一个学生和工作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地方,但是先生培养出的北大学子占了很大比重。到今日,我认为,先生培养出的弟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说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奠基人、中国考古学科体系的规划者、北大考古的引领者,恰如其分。
作为81级北大考古学生,当时有同学去侯马实习,宿先生专程前来探望,还为同学们上了一堂山西考古学的课,让我深深感到先生学问之博大精深。先生虽主攻历史时期考古,但从新石器时代讲起,体系逻辑清晰,让我真正认识到先生思考的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建设。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不仅在做学问,更在做人。他曾给同学写长信,具体到如何与地方工作者打交道。先生的风范不仅体现在扎实严谨的学风,更体现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教我们如何从一点一滴做起的精神。我们今天在这里缅怀和纪念先生,继承先生遗志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好我们本分的事情,把考古事业推向前进。
张广然(文物出版社总编辑):
众所周知,宿白先生的一系列著作都是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他对文物出版社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先生很早就与文物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61年前,即文物出版社成立的1957年,先生编写的《白沙宋墓》考古报告即由文物出版社出版。1996到1999年间,相继出版了《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等经典之作。2009到2012年,先生年届90高龄之际又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和《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其中《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辑录了先生在《文物》杂志等刊物上发表的重要论文,篇目全部是先生亲自拟定的,书的开本和篇幅也不大,但内容丰富扎实。《宿白未刊讲稿》系列6种,其中有4种收录了先生手绘的线图,实为难能可贵。上述这些著作同样值得我们后学认真研读、学习。当我们看到先生著作中的手绘线图时,倍感亲切,也从中体会到先生的认真、细致、严谨、一丝不苟。据一些编辑回忆,先生即使到了晚年,在出版著作的过程中,仍坚持亲自批改书稿校样,从不让人代劳。年届九旬的老人对待书稿严谨求实、毫无虚浮的认真态度,为我们做好编辑工作树立了榜样。而且,对于校样的修改,先生还要给编辑讲解修改的原因。这些讲解,使编辑无论在学术上还是文字上都受益匪浅。
宿先生除了署名的著作在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外,还对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重要图书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至第五批》《中国文物精华》等书稿的体例、内容予以审定,为《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撰写图版说明。做这些图书出版工作中的基础工作,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先生为文物考古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宿先生曾经对我们的一位编辑说过:“不要求每个人成为学术大家,但是,在本职岗位上做好考古学的基础工作,就是为考古学做贡献。”我们作为文物考古图书出版人,编辑出版考古报告等文物考古类图书,所从事的工作正是先生所说的基础性工作,是服务于文物考古事业、学术研究、文物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先生的话,对我们的工作是亲切的鼓励。做好文物考古图书的编辑出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宿先生虽然已经告别了我们,但是,他还留下了未了之愿。其中编辑出版《中国陶瓷史》就是其中之一。组织编撰工作的徐苹芳先生、张忠培先生也已相继离世,编撰工作遇到了巨大困难。但是我们相信,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强力支撑,有文物出版社的全力配合,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中国陶瓷史》的出版将是对宿先生的最好纪念。
为了表达对宿先生的深切缅怀,在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之际,文物出版社在第一时间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杭侃院长提出了编撰出版《宿白先生纪念文集》的愿望。今天纪念文集编撰工作正式启动,文物出版社将全力配合,做好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对宿白先生给予文物出版社的关心、支持、帮助,给予出版社的恩惠,文物出版社全体同仁将永远铭刻于心!
张连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
宿白先生出生在沈阳,在离开沈阳求学后,一直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我们多次向先生汇报沈阳考古工作取得的一些成果,先生热情地和我们一起讨论,说起家乡的一些历史建筑、民俗趣事,更是如数家珍。先生多次流露出想回家乡沈阳走一走看一看的想法,但终未能成行,成为一件憾事。
宿白先生心系家乡的考古事业。2007年,《沈阳考古发现六十年》报告卷和出土文物卷、《沈阳考古文集》结集准备出版,我们恳请先生题写书名。先生慨然允诺,并指导我们:要写好发掘简报、发掘报告,你们所做的报告,可以表达初步观点,更要紧的是如实反映古代遗存情况。
2010年,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筹备文物整理基地时,恳请先生为基地题词并为全所题写所训。先生欣然题写所训:“致学存乎心,补拙莫如勤。”
先生多次向我们强调:在城市考古中,可以对有代表性的发现做适当的保护性展示,给人们提供有意味的历史信息,反映当地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城市底蕴。而今,“清盛京城德盛门瓮城遗址”“汗王宫遗址”和“豫亲王府遗址”保护展示工程,已成为沈阳的城市新名片。
宿白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学者,是后辈学习的楷模。他的开拓创新精神、杰出成就和高尚品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青山巍巍,绿水滔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杭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
我国考古界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尊师重教。前不久,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一百二十周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寻·真——北京大学考古教学与科研成果展”。展览中有一件特别的展品,是一个放有白沙宋墓墓砖的木箱。这是一件看似普通但饱含很多内容的展品。展览开幕的时候我说过,我们用这件展品,向宿白先生致敬;用整个展览,向中国考古致敬。北大考古一路走来,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创建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还有先生未竟的事业,都是我们未来努力工作的目标和方向,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先生。
吴荣曾:我1953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宿白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中间考古专业的领导换过几波,但实际负责管理考古专业的还是宿先生。先生工作能力很强,行政工作也做得很好,从那时起,就成为考古专业的实际负责人。当时同学接触最多的也是宿先生,所以对宿先生也比较了解。课程安排、人员调配等大小事务都由先生操办。当时考古专业正值草创之时,教师紧缺,正式教师就是宿先生和阎文儒先生,其他教师都是外聘过来的,宿先生外请来的老先生很多。宿先生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开设了美术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两门课。当时人手少,宿先生主攻唐宋考古,秦汉考古请过王仲殊先生,宿先生也曾亲自上阵,并且表现出了很深的造诣。
宿先生不仅学识渊博,还多才多艺。先生有刻章的喜好,但不张扬,可能外面有很多人并不了解。先生还有一项技能,就是素描能力很高。他曾去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跟董希文先生学习素描,水平不输专业人员。总体来说,在我和宿先生这么多年的交往过程中,先生的品质可以总结为两点,一是知识渊博、二是治学谨严。
严文明:我高中时期喜欢数理化,进校本来报考的是物理系,是苏秉琦先生找我谈话我才选择了考古专业,但后来引我走上考古道路的是宿先生。苏秉琦先生是中科院考古所的研究员,在北大是兼职,不负责具体事务,印象中苏先生主要提供选择实习地点的方案,因为当时北大实习是和考古所挂钩的;而具体的教学工作,包括实习的组织,是宿先生在操办。第一次北大自己组织实习是1957年的邯郸实习,就是宿先生带队。
宿先生对于教师和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北京大学的考古教学能够走上正道,能够比较快速的发展,第一功劳当归宿先生。我做讲师的时候,讲课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宿先生来进行教学检查,提出了好多意见,有根有据,让我汗颜。这种高标准严要求,对于年轻教师的成长很有帮助。宿先生不是只对别人要求高,他首先是严于律己。
先生治学成功,有关键一条就是“勤”。先生认为早上安静、效率高,因此每天四点起床,就开始看书。这里举两个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宿先生第一次去美国,就一头扎进国会图书馆,因为那里有三本国内没有的书,他就手抄回来。后来一起去台湾开会,会议结束后台湾学者邀请我们游玩,宿先生却说这边有几本大陆没有的书,他也要手抄回来。于是我们在台湾玩了十多天,宿先生就在图书馆泡了十多天。因此宿先生的成就,跟他的勤奋有很大关系。我想起高尔基说过,天才就是聪明加勤奋,这用在宿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况且他还是比一般人更聪明,也更勤奋。正是聪明和勤奋的结合,造就出了这样一位巨匠。
宿先生对待工作同样认真,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很大程度上是在他的主持下成长起来的。当初筹备成立考古系的时候,校方对于系主任的人选倾向于宿先生。一般这种有头衔的事情,先生往往拒绝,但那次却很爽快地接受了,并让我来做副系主任。宿先生一直对考古专业和考古系的建设等教育工作十分上心,说他是中国考古教育的奠基人,毫不为过。先生是一棵参天大树,先生的业务水平我无资格评论。我们纪念、追思先生,就是要学习先生的精神,不然也不配做先生的学生。
杨泓:我是在六十五年前入学的。我入学去看望阎文儒先生,阎先生就带我去见了宿先生,我应该是班里第一个到校第二天就见到宿先生的。大二的时候跟着邓先生写论文,也是先去请教宿先生,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到大三写学年论文,就是后来的高句丽壁画石墓的文章,也是蒙宿先生的指导。可以说我学会写论文,就是宿先生带出来的,我一辈子也是沿着先生教出的道路上走。之后在中科院考古所里,就有机会和先生共事研究了,主要有两项:一是当时尹达组织编写“十年考古”,成立了编写组,宿先生是考古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组的组长就是宿先生,成员是我和徐苹芳,于是就在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工作;二是后来编写《大百科全书·考古卷》的魏晋南北朝到明清考古的学术分支,宿先生是主编,徐苹芳是副主编,我是成员,由此也就认真地跟先生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和先生六十五年的师生关系,想说、可说、能说的太多。先生的学问、人品,我是完全无法望其项背的。先生虽然一般给人的印象都是比较严肃的,但私下里其实也是个很风趣的人,之所以多数时间看起来严肃,主要是先生要求严格、做事认真。先生虽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员,但表现得比很多党员都够中国共产党要求的高标准。宿先生教我的东西我受用了六十五年。先生走了,我也没有老师了,但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学会,这也是我的遗憾。
徐光冀:宿先生确实是文物考古界的巨人、参天大树,是我们在座各位、更是考古界永远的老师。1952年,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三家合办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我是1954年入学,当时大部分教师还是外部人员,来自中科院考古所、古脊椎所(当时叫新生代研究室)、故宫等单位。北大自己的老师就是宿白先生和阎文儒先生。专业创办之时,苏秉琦先生是教研室主任,宿白先生是副主任但实际负责日常工作,很多中间的联络性工作都是宿先生在做。那时候我还是个学生,不能体会其中的艰辛;工作之后,才体会到先生当时的呕心沥血。先生对考古专业的发展实在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正是由于先生的付出,不到十年,也就是1960年前后,考古系的主要课程都是由本校教师承担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宿先生当时主要承担历史考古学的教学工作,教学内容、体系都是先生自己谋划和组织的,现在这个体系已经推广到了全国。把考古资料和文献结合,是先生创设的历史时期考古教学样板。对于历史时期城址、墓葬的研究方法,先生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初,国家文物委员会的成立,主要是为了文物保护的一些重大问题。后来委员会停止活动后,宿先生仍在为文物保护工作积极奔走,例如三峡的文物保护工作规划。在此期间,先生也确实检查了很多考古工地,直到80岁还在全国跑点。
中国考古学会是个很好的学会,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交流和团结全国的考古工作者。宿先生从一开始就是理事,而且是最年轻的常务理事,到第三次大会就担任了副理事长。1995年正处在筹备来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过程中,当时理事长苏秉琦先生住院,他给常务理事会写了亲笔信,委托宿先生主持常务理事会工作。宿先生顶着压力接下了任务,仍坚持按照会章由常务理事会组织筹备。学会作为民办组织,一直都是组织纯学术活动,受到了民政部的表扬。先生为考古界的团结作出了榜样。
樊锦诗:我们都知道,石窟寺考古的体系是宿白先生创立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是先生最关心的两个地方。先生和敦煌结缘的时间很早。解放后,文化部接管当时的敦煌研究所,就派先生来勘查,这是先生和敦煌的交集之始。1955年,正式的考古调查开始。现在人们提到很多保护方面的问题,先生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看出来了,只是那时候没有太多可以相配合的保护手段。举一个例子:刚解放的时候敦煌窟檐破败甚重,是先生按照《营造法式》的记载进行了保护修复。现在说敦煌保存下来了5座唐宋窟檐,这都是宿先生等老一辈考古人的功劳。后来也是宿先生向文化部建议,认为风沙导致石窟的断裂是敦煌面临的最大问题,才有文化部下达批示予以保护。北大的独立考古实习,第一次是去邯郸的石窟,第二次就是在敦煌。可以说,中国石窟寺考古体系真正拿出来,也是在敦煌。后来先生系统讲授了敦煌七讲,成为了敦煌研究院发展的转折点,大家才开始明白怎么搞石窟寺研究,我自己也是一生受益。我在敦煌做的一点工作,都是先生教出来的,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先生的教诲我们终生难忘。
李仰松:宿白先生培养的学生很多。我1950年就来北大了,是文学院博物馆专业第二届学生。当时,新中国刚成立,到处搞建设,经常发现文物,地方上的考古发掘水平跟不上文物出土的速度,于是北大就开办了考古训练班。训练班一共四届,培养了360多人,其中很多回到地方上都成了专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开办文物考古训练班是十分必需的,宿先生负责训练班的教务工作,很忙、很辛苦,这都是宿先生的贡献。先生去世让我很伤心,先生是我们永远的老师,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考古后辈的楷模。
雷从云:先生是一棵大树,一直心系着他的学生。先生非常关注我国文物对外交流,关心文物对外展览。1971年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成立,那时候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览工作委员会,宿先生任陈列组组长。1980年我进入交流中心,到2011年退休,在这21年间,我应该算是和宿先生接触最多的人之一。我主办的69项展览,有一半以上都请教过先生。
宿志一:说实话,我对父亲的工作并不是很了解。我走的是理工路线,对于父亲的学术路线、学术水平并没有很多概念,直到最近看很多老师对父亲的追思,才填补了我对父亲认知上的一些空白。关于父亲的为人,我就说一件事情。包括我在内,现在不少人的名片上都会印上很多头衔,但在父亲的名片上,只有“北京大学教授”一项。我曾就此问过他,他说我没有多少成绩,就是当老师而已。父亲是一位踏实、简单的人。(以上内容根据发言记录摘编而成,未经本人审阅)
责编:韩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