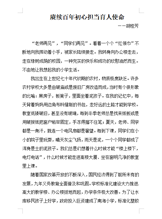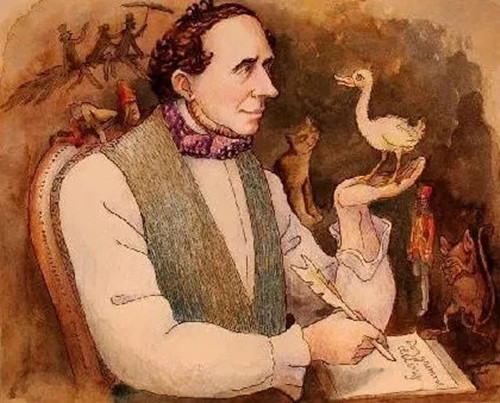《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
李新伟分享
111204
一 自在的“最初的中国”
张光直在1986年出版的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国考古学》)第四版中提出了他的“多元一体”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他将公元前4000年时期的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八个文化系统,指出,在公元前5000年以前,各地史前文化互相分立,“我们实在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这几处文化放在一起来讨论”,公元前5000左右,新的文化出现,旧的文化扩张,“到了约公元前4000年,我们就看见了一个会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的开始,那就是这些文化彼此密切联系起来,而且它们有了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这些成分把它们带入了一个大的文化网,网内的文化相似性在质量上说比网外的为大。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了解了为什么这些文化要在一起来叙述:不但它们的位置在今天的中国的境界之内,而且因为它们便是最初的中国。”“这个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开始形成,范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我们应当如何指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完全中立的名词而称之为X,可是我们也不妨便径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帝国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与其他描述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模式相比,此模式未设置中心,为客观探讨各地区的互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非常明确地以考古资料可以清晰显示出来的区域间的密切互动作为将它们维系为一个整体的纽带,并提出这种互动催生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就是最初的中国,这就为以考古学为基础重建中国古史提供了基本框架。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的时候,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在论证各地区的联系时,主要证据是陶器的形似性。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更丰富的资料,讨论“中国相互作用圈”形成的时间、各地区相互作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以及作用圈的形成与中国文明起源的关系。
由目前的资料看,此作用圈的形成约在公元前3500年至3300左右,也就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中晚期,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红山文化中晚期,崧泽文化中晚期和凌家滩遗存时期。该时期是中国史前史的灿烂转折期,各主要文化区几乎同步上演着飞跃式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区文化同步飞跃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加剧、新的社会上层闪亮登场的背景下,地区间的交流也有了质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远距离“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建立。
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和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远隔1000余公里,陶器风格迥异,但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同样以龟、猪和鸟的写实或抽象的造型为载体,表达近似的原始宇宙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M4中随葬凌家滩风格的玉人,凌家滩最大的墓葬07M23中则随葬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龟的抽象形态“箍形器”。西坡墓地和东山村墓地的最新发现表明,大口缸是另一种上层交流的重要物证。这种特殊的“大器”在豫西、山东和长江下游公元前3500左右的大型墓葬中均有出土,各地出土的器物应是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摆放位置相似,很可能反映了一种通过交流形成的、相似的社会上层葬仪。庙底沟风格彩陶纹样的传播是当时的文化交流风潮最亮丽的标志。彩陶强有力的辐射应该是以多种形式完成的,社会上层交流可能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根据目前的资料,大汶口文化墓地中,随葬庙底沟风格彩陶的多为大型墓:山东邹县野店M47,出土随葬品68件,为墓地总最富裕墓葬之一;大汶口墓地M1014和M1018也都是出土象牙发饰和数十件随葬品的大墓。值得注意的是,大汶口墓地大型墓M2005中有用黄色胶泥涂抹墓坑四壁和底部以及二层台侧壁的现象,与西坡墓地用泥封盖墓室甚至填埋整个墓圹的做法颇为相似,这些迹象表明大汶口和庙底沟的社会上层间有着特殊的联系。象牙器也是当时长江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大型墓葬中流行的奢侈随葬品,黄河流域的象牙制品或原料应是通过上层交流网从长江流域获得。这些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辨识的只是当时交流内容的一小部分,实际发生的交流要远为广泛和深入。
建立社会上层交流网是世界各地前国家复杂社会流行的“统治策略”,西方学者对此有很多精彩的研究,既有理论性的探讨,也有民族学的考察。美国学者赫尔姆斯(Helms)在对中美洲印第安人社会的研究中就发现,酋长的继承人一定要有游学的经历才有资格承继大位,他们会到著名的大酋邦“留学”,学习各种在本地学不到的知识。学者们普遍认为,建立上层交流网,获得外来的珍奇物品和高级知识,可以使统治者们获得一种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权威,对于其维护统治至关重要(Helms: Ancient Panama: Chiefs in Search of Power)。
目前的考古资料确凿证明,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同样的社会上层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凌家滩大墓07M23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亲自访问过牛河梁,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M4的墓主也很可能访问过凌家滩。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他们朝气蓬勃,充满了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其权力,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
在这一交流网中流通的不是一般的日用品和生活必需品,而是涉及宇宙观、天文历法、沟通天地的手段、各种礼仪、各种巫术和特殊物品制作技术等当时最高级也最神秘的知识,是标志身份和权力的奢侈品,是象牙和玉料等珍稀原料。各地区在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中国相互作用圈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中国的史前基础得以确立,“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形成的程序强力启动,这是真正划时代的盛事,与后来最早的“王朝”或符合西方定义的“国家”的出现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距今5000多年的史前时代, “中华文明五千年”并非虚言。有关夏代及其以前的古史记载并非后代的臆造,牛河梁、凌家滩、大汶口和西坡等墓地的大墓的主人就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们获得和维护权威、交通远方的传奇业绩,很可能就是古史传说的重要素材。从这个意义上说,距今五千年之前真的有了一个可以称作“最初的中国”的自在的实体,这个可以通过考古资料认定的实体内的各个地区通过以社会上层交流网为核心的密切交流,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可以用“中国”命名的文明的史前基因。
二 《禹贡》和最初的“中国梦”
踊跃参与着区域间交流的社会精英们是否认识到了相互作用圈的存在?答案多半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相互作用圈”诞生的同时,对这一自在实体的认知也已经开始形成。我们不能低估那些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建造复杂的建筑、绘制生动的彩陶、制作精美玉器的社会精英们的能力和智慧。相信他们在每一次远游后,都会以某种方式记录见闻,勾画最初的“山海经”和“九州图”,展示给本地民众,并将其作为新的高级知识传授给子孙后代。经过若干代人的积累,相互作用圈的地理范围、山川形势和物产人文很可能已经成为各地区社会上层的高级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部分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已经成为社会上层的必修课。从这一角度说,参与了互动的各地区社会精英们是“认识”到了相互作用圈的存在的。但他们未必已经认为这一作用圈内的各个人群属于同一个“族群”,围绕着共同的“花心”。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在相互作用圈形成时期,各地区虽然密切交流,但都各自沿着自具特色的文明化道路独立发展,红山社会和凌家滩社会宗教气氛浓重;大汶口社会和崧泽社会墓葬奢华,但更重视世俗权力;庙底沟社会有大型聚落和大型公共建筑,但大型墓葬中没有奢侈随葬品——各地区的社会上层明显在使用不同的领导策略获得和维护权力。因此,相互作用圈在他们的认知中,可能只是一个区别于蛮荒之地的可以交流的“世界”或“天下”。也就是说,作用圈内的各文化区已经认识到他们拥有同一个世界,但是他们还没有同一个梦想,一个促进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
那么,最初的“中国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禹贡》应该是这个“中国梦”的较早的完整版本。学者多将其当做地理书研读,但其实这部著作的一个主旨是以禹开山导川,治平水土的英雄业绩,将九州连接为一个整体,是推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极具政治智慧的宣传方案:“禹迹”所到之处,如文明之光普照,宜居宜耕,物产丰富。禹迹覆盖九州,使之成为与蛮荒之地迥然有别的文明世界。因为禹的功绩,九州成为一体有了充分的理由,一体的九州由一个像禹一样的圣王统治、四方朝服纳贡也有了充分的理由。
有学者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禹贡》成书于战国时期,但正如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所言,西周初期应该就已经形成了《禹贡》的基本内容。《尚书•立政》是周公告诫成王的诰文。其中有“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禹迹”对应“天下”。周公提出要经营洛邑,占据天下之中时,他胸怀中的天下,应与九州范围大体一致。周代的政治家们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一“大一统”口号时,其依托就是天下均为禹迹,本应一体,由一人统治的政治理念。
极力宣传“大一统”思想的周初政治家们是否就是大禹政治神话的最初作者呢?《诗•商颂》中有“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九有有载”“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等与大禹传说有关的内容。虽然《商颂》为春秋宋人的作品,虽然甲骨文中未见“禹”字和九州等与禹的功业相关的内容,但禹的政治神话很可能在以中原为核心统治区的商代即已经出现。考古资料和甲骨文均显示,占据中原的商与周边地区的交流非常密切。他们从四方获取铜、锡和铅等青铜器铸造所需的原料,也获取玉料、大龟、海贝、象牙等珍稀材料。这些物品有些是四方以“内”、“入”等形式贡献而来的,有些则是“取”来的,取的方式当然包括武力。商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辐射力,商风格的青铜礼器在周边各地均有发现。很明显,与周人一样,商人在构思自己的王朝时,无疑也是胸怀与九州的范围大体符合的“天下”的,他们也许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实现各地区的一体化,进而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中国梦”,但至少已经有了宏大的理想政治地理蓝图,在此蓝图中,商人自己居于核心地位,势力强大,四方“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只是商人实现这一蓝图时可能更倚重“帝命”、倚重祖先在天帝左右的特殊关系,也倚重武力,不大重视大禹政治神话促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软实力”。这也许与这一神话为被他们“革命”掉的夏王朝歌功颂德有关。

汉画像石中的夏禹

殷墟妇好墓出土嵌绿松石象牙杯
其实,如果说禹的政治神话在商代已经出现的话,夏人自己应该是大禹政治神话最可能的创作者。但夏王朝是否存在过,在考古界还是个存在严重争论的问题。要求最严格的学者甚至提出只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资料,才能确凿肯定夏的存在。在考古未发现夏代文字、文献又都形成于后代、不能排除后人附会的情况下,不可能确凿地讨论大禹神话是否为夏人自创。
考古资料可以确证的商代之前的文化和政治中心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也是占据中原,地望正在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中心地区,碳十四年代约相当于依据文献记载推算出的夏代后期,社会发展程度也达到了“广域王权国家”的标准(许宏:《最初的中国》),被很多学者认定为夏后期的都邑。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文化与周边地区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与商王朝和周边的联系相似,同样布局宏大、有取有施。二里头遗址发现有来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与东方、西北方和南方文化相似的玉器。在盛产铜矿和食盐的中条山脉及运城盆地,在铜矿资源最丰富的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发现有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遗址,很可能与二里头获取资源的努力有关。更有资料表明,为了获取铜和铅,二里头与辽宁西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以各种方式获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同时,二里头文化也表现出强大的文化扩张力,“向四围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 (许宏:《最初的中国》)。�(�)、爵等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由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一带,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一带。二里头风格的玉璋向南传播至南阳盆地,再南下到达长江中游湖北、湖南一带;再向南,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乃至越南北部都有发现。这种强势的大范围传播,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物推广和接受,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联系。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
可见,二里头的领导者们也是胸怀天下的,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范围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传播礼仪。这种强大中心为主导的互动,客观上肯定会促进参与互动的各个文化区的一体化。在此情势下,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否主动以创作政治神话的方式,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并心怀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梦想呢?目前的考古资料虽然让我们难以对此作出证明,但也明确提示我们,二里头的统治者是具备实施这种主观努力的政治动机、知识储备和运作能力的。
再向上追溯,年代约为距今4500年至4000年的陶寺文化已经开创了这种占据中原、势力超群、联系四方的政治格局。该文化的都邑性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其地望正是文献记载中尧的活动中心区。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曾精辟地指出:“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庙堂礼乐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红山文化更高一级的国家形态。圆腹底�、鬲原型可追溯到内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绘龙纹与红山文化有关,扁陶壶序列的近亲只能到山东大汶口文化寻找,俎刀更要到远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亲。••••••陶寺遗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有学者进一步提出,陶寺的陶豆来自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陶罐形�来自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玉琮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鳄鱼皮制作的“�鼓”来自山东龙山文化;铃和齿轮形器等铜器则可能受到西北地区的影响。值得关注的是,陶寺显贵阶层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琮、俎刀、�鼓等仪式用品,很明显,拥有来自四方的珍稀物品、融合四方礼仪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重要的领导策略。这些领导者们无疑也是胸怀四方的,而且重视自己在四方中的地位,这种胸怀和重视为从文化心理上推进各地区一体化的进程,至少从理念上构建一个广域统一国家的梦想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陶寺遗址出土良渚文化风格玉琮
对于一些严谨的考古学者来说,是否有夏,尚且存疑,是否有尧,更似乎连讨论的空间都没有了。但陶寺遗址的考古资料清楚地向我们显示,在“疑似”夏代后期的二里头文化之前数百年,已经在中原地区出现了胸怀天下的领导者。他们对当时已经形成了约1000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的认知和构想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能低估这些可以建造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城郭和结构复杂的天文观测设施、可以汇纳四方物品和知识的先贤的能力和智慧,他们很可能通过实施各种领导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做到《尚书•尧典》中提到的“协和万邦”。尧分命羲和、羲叔、和仲、和叔宅于四方,“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也许不能仅以“传说”视之,而可能是与“地理版”的《禹贡》政治神话功能相同的、“天文版”的促进各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最初的中国梦”。

南宋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之《九州山川实证总图》
苏秉琦在1991年发表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中对“‘中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视野宏阔的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三个阶段。目前的考古资料显示,距今约5500年初步形成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参与交流互动的各地区对这个中国应该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并启动了张光直所说的“持续一千多年的有力的程序”。在相互作用圈发展了约1000后,距今约4500年,陶寺文化在广义的中原地区灿烂登场,为赵辉曾论及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揭幕,造就出胸怀天下的领导者,开始构筑“理想”中国的最初“中国梦”,在夏商周三代的不断努力下,各地区一体化和认同感不断加强,秦汉帝国最终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形成了“现实”的中国。
相信随着资料的积累,随着考古学家和古史学家由单纯疑古向科学释古的转变,我们对这一波澜壮阔进程的认识会更加清晰,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讨也会更加深入。
(作者单位: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禹会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8月)
(作者单位:李新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原文发表于,《禹会村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8月)